作者:刘珂(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疫情爆发以来,各国政府采取了严厉的“保持社交距离”措施以防止疫情继续扩散。许多企业基于政府要求和员工健康的考虑关闭了工作场所,非必要岗位的员工只能居家工作,由此展开一场规模前所未有的全球性远程办公实验。一时间,阿里钉钉、腾讯会议等在线办公应用迎来了巨大利好,“云办公”成为了备受推崇的新型工作模式,脸书、推特等硅谷巨头甚至允许一部分员工永久在家办公。毋庸置疑,远程办公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正常运转,减少了企业的经济损失,缓解了疫情对就业的负面冲击。但是,在疫情之下,远程办公真的有那么美好吗?恐怕,这还要打一个问号。
远程办公加剧不平等
病毒面前,真的“人人平等”吗?至少在远程办公的可行性方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远程办公并不适用于所有职业。例如,服务生只能在餐厅为用餐者提供服务,牙医只能在诊所对病人进行诊断,销售员只能在商场和顾客进行接触。相较于其他适合远程办公的职业而言,这些职业的工作者更容易由于疫情期间工作场所的关闭而失业。这些工作者不仅在短期内收入降低,也会由于工作经验的缺失和工作技能的生疏而丧失竞争力,从而在疫情结束之后更难重新找到工作。即使宽松的社交距离政策使得这些员工仍然可以在工作场所正常上班,他们也会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
Dingel & Neiman(2020)即将发表于“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的文章根据远程办公的可行性对所有职业进行了分类。在非疫情时期,即使某项工作具有远程办公的可行性,企业和员工仍然可能更偏向于在工作场所办公。而在疫情之下,由于工作场所的关闭,远程办公往往成为企业复工的唯一选择。因此,使用非疫情时期远程办公的历史数据来预测疫情期间远程办公的应用情况会存在偏差。为了避免这种偏差,该文章使用了美国劳动统计局职业信息网络O*NET(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Network)的调查数据,根据每种职业包含的技能要求、是否需要在户外工作、是否需要和同事或顾客保持近距离等信息来衡量该职业远程办公的可行性,从而对疫情期间远程办公的实际数据进行预测。其研究发现:在美国最多有37%的工作可以完全远程办公,这些工作往往收入更高,其工资占据了全美所有工作工资的46%。在不同地区和行业中,具有远程办公可行性的工作占比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例如,在金融、公司管理、教育、法律以及专业性和科学性的服务行业中有更多工作适合远程办公,而与农业、酒店餐饮和零售有关的工作远程办公的可能性较低。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远程办公的可行性更低。Saltiel(2020)通过分析世界银行STEP(Skill Toward 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的住户调查数据发现:在该调查所涉及的十个中低收入国家中,只有13%的市区员工具有远程办公的可能性(如果考虑农村人口,这一比例将更低),且这一指标在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其中最高达到23%(中国云南省),而最低只有5.5%(加纳)。远程办公可行性较低的工作者一般是经济上的弱势群体(Mongey et al., 2020)。具体而言,他们更可能具有以下特征:单身、没有大学学历、处于收入分布的底层、流动资产占收入的比例较低、非全职工作、没有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通过租房生活等。
远程办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性别不平等。Alon et al.(2020)发现由于男性相对于女性更有可能从事远程办公可行性较高的工作,女性受到疫情影响失去工作的风险相对更高。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往的经济衰退中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反而更容易失去工作。这是由于那些“标准”的经济衰退主要影响以男性工作者为主的制造业和建筑业,而女性主要集中在医疗、教育等非周期性行业工作。但在本次疫情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是女性工作者居多的餐饮、住宿等服务行业,原因之一就是这些行业基本无法实现远程办公。另一方面,即使家庭中的夫妻双方均可以在疫情期间实现远程办公,远程办公本身也会在在工作与家庭角色的冲突方面对夫妻双方造成不同影响。例如,母亲往往比父亲承担更多家务,而相对于无法远程办公的家庭而言,在夫妻双方均可以远程办公的家庭中这一性别差距会更大,且在疫情期间远程办公的母亲往往比远程办公的父亲更容易产生焦虑、孤独、沮丧等不良情绪(Lyttelton et al., 2020)。
远程办公真的有效率吗?
在远程办公模式下,员工是否能维持高效率成为了企业管理者最担心的问题。IBM是最早引入远程办公制度的企业之一。早在1983年就已经有约2000名IBM员工在家工作,到2009年IBM宣称其在全球173个国家里有40%的员工实现远程办公。继IBM之后,雅虎、百思买等知名巨头也都纷纷推行远程办公模式。然而在2013年,雅虎和百思买先后宣布放弃远程办公,而在四年后的2017年,一向被外界视为远程办公鼻祖的IBM公司也由于连续20个季度收入下滑而对员工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回到办公室、要么离开公司”。这些企业对于远程办公态度的转变,主要原因是其管理者认为“远程办公难以保证员工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合作,无法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因此往往会降低工作效率和质量”。
远程办公可能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远程办公不利于团队合作。Battiston et al.(2018)发现团队成员之间面对面的沟通会使工作效率比只允许电子通讯交流时更高。当工作内容越是紧急、复杂和偏向信息密集型,或工作团队的同质化程度越高时,这种效率差距就会越明显。在他们的实验中,警察局的接线员将紧急情况报告给相关地区的决策人,当接线员和决策人在同一房间内并可以面对面沟通时,决策人做出决策所用的时间更短且随着两人在房间内距离的拉近而降低。Lee et al.(2010)发现当同一论文的合作者在同一地点办公时,论文的引用率(衡量论文质量)更高。第二,远程办公无法产生同群效应。Mas & Moretti(2009)发现在一家连锁超市里,不同收银员的工作效率之间会相互影响:当员工发现同事都在努力工作时,员工自己也更有激励去努力工作而不会选择去“搭便车”。这是由于当某个员工不努力工作从而间接加大了同事的工作量,且被同事察觉到自己没有在努力工作时,员工自己会感到一种“社会压力”,例如担心被同事厌恶、感到羞愧等。因此,在远程办公模式下,由于员工的偷懒行为无法被同事察觉,这种“社会压力”可能不复存在,员工也就失去了努力工作的激励。第三,远程办公模式下员工监控和绩效考核难以进行。随着监控技术的不断进步,远程办公的企业已经开始使用IT解决方案来监控员工。然而,如果远程办公的工作任务不通过互联网进行,远程监控就难以实现,员工仍然可能在家偷懒。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员工的投入(例如工作时间)无法被观察或核实,为了激励员工努力工作,绩效工资应该是基于员工的产出而非投入。但对于某些工作任务而言,员工的产出也难以被准确衡量,例如某些工作的绩效需要主观评估或工作内容涉及到难以核实的信息等,因此基于员工产出的绩效工资也可能无法提高工作绩效。另外,如果企业管理者和员工之间存在双向的信息不对称,即使企业管理者声称员工受到远程监控并且真的可以实现,员工也可能并不相信企业有能力或有意愿对其进行监控,因此无法达到激励员工的目的。
远程办公的支持者往往会引用Bloom et al.(2015)发表于“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文章作为远程办公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的证据。该文章基于对中国旅游公司携程的约1000名呼叫中心的客服人员进行的为期9个月的随机对照试验,发现远程办公可以使员工的工作绩效提高13%(相当于每周额外多出一天的工作产出):其中9%来源于通勤、休息时间和病假的减少导致的工作时间的增加,4%来源于安静的工作环境导致的工作效率的提高。然而,上述结论可能并不适用于当前环境下的所有企业。首先,该研究的设定并没有考虑疫情期间许多可能妨碍远程办公效率的因素。例如,“保持社交距离”措施导致学校关闭,家长需要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在家办公的最大挑战是家里孩子不上幼儿园”;实验中获准远程办公的员工在家都必须拥有专属的工作空间从而不被家人打扰,而当前许多员工被迫在狭小的卧室、充满噪音的公用房间或无线网络较差的地区办公,且随时需要抵挡冰箱、床和手机的诱惑;实验中远程办公的员工每周仍然有一天需要回办公室上班,这对于保持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至关重要,而在疫情期间员工往往只能持续在家办公;实验中员工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偏好和之前的远程办公经历自愿选择是否在家工作,因此实际进行远程办公的员工相对于其他员工而言往往更加适合这种办公模式,而这种“选择效应”在当前环境下难以实现。第二,远程办公能否维持高效率应取决于工作类型。实验中远程办公之所以能提高绩效,一个关键原因是呼叫中心的工作比较适合远程办公:员工之间不需要团队合作或面对面的沟通,员工的工作绩效容易量化和评估,且携程内部的数据库可以每天对员工的投入进行远程监控。然而,并非所有的工作都具有这些属性或条件,因此远程办公对不同工作类型的效率的影响也有所区别。例如,Dutcher(2012)发现远程办公由于使工作安排更加灵活,有助于提高具有创造性的工作类型的效率,但反而会降低单调枯燥的工作类型的效率。
员工支持远程办公吗?
即使远程办公可以维持高效率,使得企业愿意接受和鼓励这种工作方式,我们还要问:员工也支持远程办公吗?上文中提到的Bloom et al.(2015)还发现,远程办公显著提高了员工对工作的满意度,同时使员工的离职率大幅下降:在实验进行的9个月中,远程办公的员工的离职率仅为17%,而在办公室工作的员工的离职率为35%。然而,在实验中获准远程办公和实验前申请了远程办公但未获批准的员工中,有50%在实验结束后改变了想法:他们希望回到办公室工作。而在实验前没有申请远程办公的员工中,仅有10%在实验结束后表示希望可以远程办公。那么,如何解释员工这种看似矛盾的选择呢?首先,一部分远程办公的员工表示,由于缺乏同事和上下级之间的社交互动,容易产生孤独和沮丧感,长此以往会影响员工个人的身心健康。第二,在给定工作绩效的情况下,远程办公降低了员工的晋升率,因此不利于员工长期的事业发展。对此,员工和企业的管理者给出了以下几种可能的解释:远程办公减少了员工参加工作培训的机会,不利于员工技能的提升;远程办公的员工缺乏和上级面谈的机会,因此员工的工作成果不容易被上级关注和认可;远程办公的员工相对缺乏培养人际交往能力的机会,因此难以胜任管理层的职位。
第三,在很多情况下远程办公不仅是工作地点的改变,同时也是工作时间的改变,但后者不一定是对员工有利的。最近网络上流行这样一句话:“如果说在公司办公是一群人的996,那么远程办公就是一个人的007。”疫情期间,许多被迫远程办公的工作其实并不适合远程办公,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工作难以实现远程监控和绩效考核。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即使员工在家努力工作,老板往往也会默认员工在家偷懒,并提出员工在非工作时间加班这种在老板看来“合情合理”的要求。由于工作和生活边界的弱化,员工往往没有下班、周末的概念,有些老板甚至要求员工24小时随叫随到(且没有加班费)。Mas & Pallais(2017)发表于“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文章通过离散选择实验研究了员工对于不同工作安排的偏好。具体而言,研究者在某大型招聘平台上贴出只包括工作内容(呼叫中心的电话调查员)和任职要求等信息的招聘启事,并在随后的申请过程中询问求职者对于各种工作安排和工作报酬的组合的偏好。该研究发现:给定每周工作的总时长,平均来说,求职者愿意放弃8%的薪水以换取在家远程办公的机会,但同时愿意放弃20%的薪水以避免那些雇主可以随意安排工作时间的工作。因此,如果远程办公意味着员工需要随时响应,在薪水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员工宁愿选择在办公室工作!研究还发现,员工之所以讨厌雇主对工作时间的随意安排,并不是由于工作时间难以预测导致的随机性,而是由于员工不喜欢在深夜和周末等非常规的工作时间上班。
总而言之,对于许多工作者而言,远程办公就像钱钟书先生笔下的“围城”:曾经在办公室坐班时,我们憧憬SOHO的感觉,而真正开始远程办公之后,我们又想回到办公室上班。疫情使远程办公更加普及,但并非所有群体都会因此受益。作为企业复工的权宜之计,远程办公也会给企业管理带来各种挑战。不管怎样,疫情结束之后在办公室上班的工作模式可能还是会回归主导,相信人们都会珍惜和怀念这一段远程办公的特殊经历和体验。
参考文献:
[1] Alon, T. M., Doepke, M., Olmstead-Rumsey, J., & Tertilt, M. (2020),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gender equality”, NBER Working Paper No. 26947.
[2] Battiston, D., Blanes i Vidal, J., & Kirchmaier, T. (2017),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in organisations”, Working Paper.
[3] Bloom, N., Liang, J., Roberts, J., & Ying, Z. J. (2015), “Does working from home work? Evidence from a Chinese experi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0(1), 165-218.
[4] Dingel, J. I., & Neiman, B. (2020), “How many jobs can be done at hom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accepted.
[5] Dutcher, E. G. (2012), “The effects of telecommuting on productivity: An experimental examination. The role of dull and creative task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84(1), 355-363.
[6] Lee, K., Brownstein, J. S., Mills, R. G., & Kohane, I. S. (2010), “Does collocation inform the impact of collaboration?”, PloS one, 5(12), e14279.
[7] Lyttelton, T., Zang, E., & Musick, K. (2020), “Gender differences in telecommuting and implications for inequality at home and work”, Working Paper.
[8] Mas, A., & Moretti, E. (2009), “Peers at work”,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9(1), 112-45.
[9] Mas, A., & Pallais, A. (2017), “Valuing alternative work arrangeme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12), 3722-59.
[10] Mongey, S., Pilossoph, L., & Weinberg, A. (2020), “Which workers bear the burden of social distancing polici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7085.
[11] Saltiel, F. (2020), “Who can work from hom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vid Economics, 7, 104-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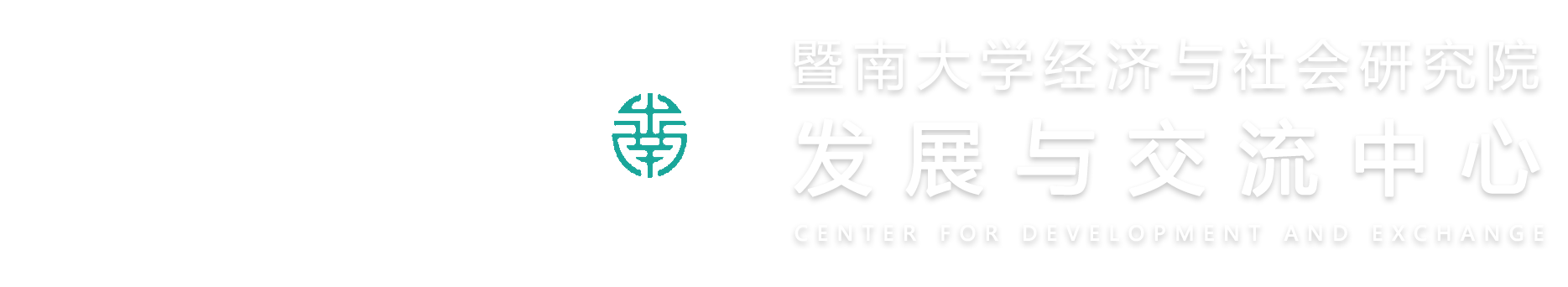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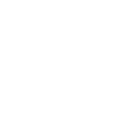 EDP论坛
EDP论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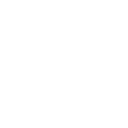 资料下载
资料下载 招生简章
招生简章 校友组织
校友组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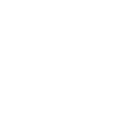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601号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601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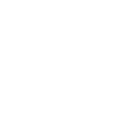 IESR邮箱:iesr@jnu.edu.cn
IESR邮箱:iesr@jnu.edu.cn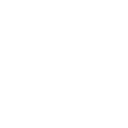 邮政编号: 510632
邮政编号: 510632